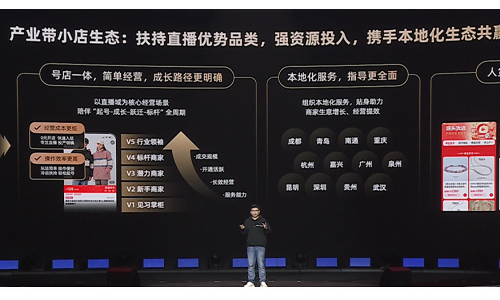何任远
这里没有西欧,特别是德国那种冷峻严肃的建筑语言,也没有俄罗斯傲然挺立的肌肉感,然而我在这片土地上亲身感受到的文化底蕴,却让人倍感温暖和亲切。归根到底,也许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人,包括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内的作为个体的充分尊重。
经过12个小时的漫长空中飞行,我在4月12日傍晚降落在华沙肖邦国际机场。在跨越西伯利亚上空的飞机上,我看完了前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的作品《伊凡雷帝》。拍摄于1943年的黑白电影讲述了沙俄帝国第一任沙皇为了走上强国之路而出兵征服邻近喀山汗国、平复诸侯的故事。影片充满了斯拉夫民族的强悍,片末雷帝手握权杖在高山上俯瞰臣民的镜头,更加让人感到影片制作者对强人领导的崇拜。
相比起俄罗斯的强势和粗犷,波兰这个以伟大作曲家命名机场的国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四月的华沙乍暖还寒,古朴的建筑到处都镶嵌着曾经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名人纪念碑,白鸽穿梭于人流之中,偶尔停在古老的雕塑头顶,审视着过往的人群,和来自远东的我。
走在华沙大学门外的街头上,我与人们的目光偶尔接触,对方投来了善意的微笑;在那个崇尚强者的俄罗斯,我可没有遭遇到这种让人感到暖心的微笑,唯一深刻的记忆是被莫斯科机场安检粗声粗气地勒令脱裤子,擦肩而过的几个俄国年轻人还用轻蔑的目光一边看着我一边讥笑。游走华沙街头,感觉这里没有西欧,特别是德国那种冷峻严肃的建筑语言,也没有俄罗斯傲然挺立的肌肉感,然而我在这片土地上亲身感受到的文化底蕴,却让人倍感温暖和亲切。归根到底,也许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人,包括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在内的作为个体的充分尊重。
“惊悚”的罗兹
波兰有着不少风景优美的历史和文化名城,华沙、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和洛茨瓦夫等地都是很多游客首选的地方,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游客期待的那种美轮美奂。位于中部地区的罗兹,对于初来乍到的人来说甚至有点惊悚:当汽车进入罗兹市中心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我看到了一排接一排破败灰黑的苏式建筑,熏黑的外墙和路边荒芜的草地让人感觉非常不好。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进城道路的车程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连国内三线小城都不如的荒凉县城。车停下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路灯昏暗,巷子里的苏联式宿舍漆黑一片,远处不断有警车呼啸飞奔,让人不由得担心这里晚上的治安。
第二天一早,浓雾锁城。我提起胆量在住宿地外面的街道上散步,心里始终担心会有光头党或者新纳粹青年跑出来打人。还好,迎面走来的一个小伙子,戴着大耳机,看到了我一个亚洲人独自走在街上,轻轻地向我挥了挥手,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在内街有延绵不断、形状各异的砖屋,一排排地延伸向远方。这些红色的砖头房子颜色格外扎眼,述说着罗兹工业立市的历史:这个在19世纪中叶诞生的城市,—直是中欧地区纺织工业的重镇。这个诞生在沙俄帝国占领下的工业城市,在19世纪产出的纺织品从欧洲中部一直进入俄罗斯腹地,直抵北美阿拉斯加。
这些红色的楼房,大多数是19世纪以来犹太商人修建的纺织厂房。这些100多年遗留下来的老厂房,并没有被拆掉。尽管这里的纺织业已经破落,人们却没有试图抹去这座城的历史。为了弥补工业的空心化,文化产业自然被拿作挽救经济的救命良药。
“贫穷但性感”
所谓“文化产业”,其实是从英国1990年代引进过来的经济概念,它包括了影视、设计、音乐、戏剧和建筑等领域,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运行,政府在其中起扶持的作用。这些富有特色的厂房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罗兹当地市政府用作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使用。对弱势文化工作者的照顾和扶持,是这座城市为了再次凤凰涅槃的一条道路。
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时间里,大部分包括前东德在内的东欧经济都一度陷入低迷,以租金低廉为突破点的德国首都柏林率先提出“贫穷但性感”的口号,把大量废弃的国企厂房以低廉的价格租给艺术家和初创文化企业开发。在短短十几年间,曾经被战争和经济萧条摧毁的东部柏林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文化艺术社区。然而,柏林“贫穷但性感”的策略并非不受诟病,随着柏林经济慢慢恢复,租金越来越上涨,商业味道也变得浓厚起来。
好像罗兹这样的波兰工业城市,成了下一轮文化产业孵化器的转移地点。在硕大的红砖厂房里,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可以以一个月500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租用一个几乎100平方米的办公室,这在寸金尺土的中国大城市几乎难以想象。“这真是单纯为了文化工作者生存的基础设施了!”我当时这样想。
当然这种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在欧洲有很强的公益性,是纯粹的公共服务项目而非地产投资项目。欧盟和罗兹市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基金,能够获得孵化器辅助的工作室、团队甚至个人都要经历非常严谨的筛选过程,而且在这个地方享受的优惠政策不能够超过3年。为了达到整个社区文化氛围的最大优化效果,厂房里的孵化器特别筛选了几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家进驻:时装设计师、电影工作者、家具设计工作室、魔术师、美食设计师、戏剧团体和音乐工作室都交错地在这里扎根。
在阴冷的北风吹拂下,罗兹远处的施工地盘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赢得小型世博会的主办权,罗兹这次可以说是要下定决心改头换面。艺术和文化通常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根萌芽,眼前的罗兹,这里一个工地,那里一个厂房,突然又冒出一两个电影工作室,俨然一切都是一个半成品,我们的导游笑说,这是“乱七八糟主义风格”;在我看来,这个欧洲的后发之地有点像现在亚洲那样跃跃欲试的感觉。也许过了几年之后,罗兹将会真的完成一次让人瞩目的华丽转身?
小书店的启示:咬紧牙关与文化自尊
波兰著名女记者Agata Pyzik曾经大肆鞭挞“贫穷但性感”的文化商业模式,认为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始终对波兰等东欧国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殖民意识”,以“贫穷”为自己卖点把自己不好的一面以迎合西方的视觉展示出来。然而在罗兹这座经济面临严峻转型问题的城市里,我看到的却是人们的文化自尊和自觉。
就在同一天里,我从那一片红色砖房子走到了罗兹一条全长5公里的商业步行街。相比起国内,这条名为Piotrkowska的步行街人流并不频密,两边的房子古色古香,保存了几乎一个半世纪,没有遭到二战的破坏。在这条街上,诞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阿瑟·鲁宾斯坦,短短的5公里步行街就有几乎5间实体书店。
在这些书店里,我看到的是从容与淡定,售卖古典音乐唱片的老人与另外一位顾客用波兰语侃侃而谈,从发音中可以听出提到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名字。在这样一个略显冷清的城市唱片店里,我看到了种类最齐全的唱片编目,特别是波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都能够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找到:肖邦、席曼诺夫斯基、维尼亚夫斯基、帕努夫尼克、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和格雷茨基等重要作曲家的全集,都被这位西装笔挺、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绅士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不由得佩服这位老先生的功力,仿佛一部波兰20世纪的音乐历史都被他整体搬到了这家书店了。
拿着一大袋唱片,我走进了隔壁的一个小咖啡馆,实木家具和墙壁的装修,色调温暖,产生一种踏实感,衣着整齐的中年人在角落看报纸,仿佛让人回到了卡夫卡的年代。墙上镶嵌着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伟大女诗人辛波斯卡的摘录,我看不懂墙上的句子,于是我马上向一位店员询问。“我的英文水平配不上翻译辛波斯卡的字句,但是我会帮你查找,”年轻的女店员这样回答。没多久后,女店员拿着手机找到我,让我看到了她从网上查找回来的大致翻译:“当一个人面临考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到底会变成怎样的人。”
用这句话来形容罗兹的文化生活最好不过了:此时此刻的罗兹正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挑战,上世纪90年代的加工制造业向亚洲转移让这里几乎成为空城,可是这里的文化生活依然有条不紊,从咖啡店、书店、步行街和商业空间这些细微的地方,都能够看出文化早已经不只局限于高高在上,而是融化在街头的角落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这里普通人的生活是有文化的,这里的文化是进入普通人生活的。此时的罗兹,在我心中的印象与我刚到的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依·瓦依达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无辜的通灵人》。在电影里,1950年代的华沙依然是一片颓门败瓦,然而年轻人们压抑不住旺盛的创造欲望,拿起爵士鼓和小号,让飘渺散漫的乐音在战后华沙的瓦砾中穿行——这个情景让人感到这片废墟其实依然生机蓬勃,对这里的明天还怀有希望。今时今日的罗兹不是被战火摧毁,而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社会剧变的后遗症依然在这里历历在目,但是这里的人就好像影片中的爵士乐手那样,即使生活要让人咬紧牙关,但是依然保持着体面的文化自尊和清明自觉。
华沙:被打破的文化壁垒
如果说罗兹依然在挣扎的话,那么《天真的通灵人》中那个被夷为平地的华沙,到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华美精致的中欧首都。如果说罗兹的文化生活是朴实淡雅,散存于普罗大众的话,那么华沙作为一国之都是否也就意味着文化生活已经形成了高度,艺术家和民众之间重新筑起了围墙呢?
在回国前最后一晚,我受到一位波兰音乐行内人的邀请,到位于总理府附近的Syrena剧场欣赏波兰著名的国内爵士乐队Woitek Mazolewski五重奏的演出。提到这个Mazolewski,他可以说是波兰国内年轻人的偶像,频频出现在波兰的电视、广播、网络视频和大型露天音乐会上,在欧洲的爵士乐版图上也有自己的位置,用“网红”来形容也不为过。
由于一个小小的沟通误会,我以为要自己前往剧院后台,于是只能够向守门口的小哥说明情况。要知道,一个身无凭证的独立个人要在国内走进一个演出单位的后台几乎是难于登天的事情,我自然也不抱希望。然而那个守门口的小哥听我说完之后,马上说:“我马上就带你去后台……当然你不要紧张,即使找不到人你也有机会免费听到这场音乐会。”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以为我是来“白撞”看免费演出的。然而小哥殷勤带着我跑到剧院的后台,大名鼎鼎的Mazolewski正在忙着准备演出,其他成员也各忙各的,小哥连续问了几次都没有消息。还好这个时候,我认识的朋友才姗姗来此,避免了更多的尴尬。尽管很不好意思,我却阴差阳错地闯到了人家演出单位的后台,演出单位常见的那种壁垒就好像不存在似的。当然,我还来不及庆幸自己独闯后台的“特权”,演出结束后剧场酒吧就举行观众心得分享会,那个出现在各大唱片封面和电视荧幕上的爵士音乐家,此时正拿着啤酒与观众侃侃而谈。对于波兰艺术家来说,与受众们打成一片已经是平常事。
越经历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各种场合,我越发认同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话:“边界是用来打破的。”当我们把文化供奉在要给高高在上的圣坛,与普罗大众脱离交流和讨论的时候,人们心中自然产生自卑和壁垒。成功跳上神坛的“文化人”,有了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资格,而坐在台下的芸芸众生,则对其顶礼膜拜。文化无需要被神化,它更加需要对普通个体的关怀,以及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流和探讨。
从波兰回国,在西伯利亚的上空,我又重新看了一次《伊凡雷帝》,饰演沙皇的苏联演员那阴冷狠毒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波兰历史上没有伊凡雷帝这样好勇斗狠的君王(不得不提的,是伊凡雷帝亲自用权杖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今天的波兰在欧洲只是一个小康又平凡的国家,但是波兰普通人的文化自尊给我好好上了一课。